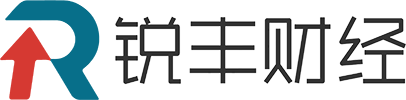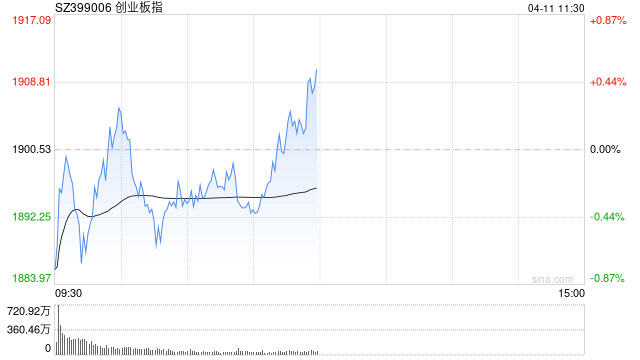当前,世界经济的变化比想象中更复杂。除了参考国际机构的判断,我们还需要深入剖析正在发生的事情,这对于深入理解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是非常重要的。
在后疫情时代,主导全球经济增长的中期因素不会发生变化,但会有阶段性不同。在以往对全球经济增长长期停滞的研究中,我们提炼出了很多基础性因素,比如全球生产率下降导致经济增速放缓。
从目前来看,各国劳动生产效率增速都在放缓,且近年来加速下行,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后疫情时期的修复比想象得要慢,疫情带来的疤痕效应较大。二是美国挑起的技术战、“脱钩”,以及“去风险”带来全球技术贸易的下降,直接导致全球技术进步增速渐缓,主要体现为全球芯片、半导体等高新技术产品交易额大幅下降。三是新技术应用场景的拓展速度放缓,主要体现为全球专利技术下降。
以上几大因素导致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趋缓,导致经济增速下降。除此之外,一些长期因素,比如人口问题、产业链供应链重构问题、逆全球化问题、减碳带来的气候成本扩张问题,以及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导致各国国防支出成本上涨的问题等,也会使得经济增速放缓。
全球通货膨胀率在2022年达到历史新高9.2%,以美国、欧盟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全面收缩货币政策和金融条件,直接导致全球融资成本上涨,投资下滑,进而遏制了快速上升的通胀率。因此,市场预测全球通货膨胀率可能会回落到5%左右。
通货膨胀率的回落对于全球经济增长,以及低收入人群生活成本的降低是一个利好消息,但与此同时,考虑到通胀的黏性依然较大,要回落到各国的通胀盯住目标值可能还需要较长时间。比如一些国际机构预计,全球通胀率回归疫情前水平可能还需要一年的时间,这意味着货币政策的逆转速度可能没有想象中快。
尽管美联储去年12月的公告中出现了全面停止加息的声明,欧盟也开始讨论利息政策的调整,但利率水平是否会有明显回调,从而带来全球金融条件及全球资本流动的逆转,依然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不过可以明确的是,全球正处在一个去通胀、去高利率的新进程中。
尽管2022年全球供应链有所恢复,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疫后反弹,但当前世界贸易仍处于收缩过程中。我认为,今年贸易实现增长是比较困难的。
2024年的贸易发展状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美国采取制造业回流、“脱钩”“去风险”等全球布局的调整已经过了5年时间。在此过程中,会产生一个过渡态,即在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的作用下,对于固定资产投资、能源等的需求有所上升。
过去几年中,中国与美国近岸外包的主要基地墨西哥的贸易同比增长非常快,对美国布局友岸外包的区域,特别是东南亚的贸易也出现了大幅增长。这些提升可能是贸易政策调整带来的结果,但更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政策再布局所带来的“引致需求”,尤其是对机电产品、新能源产品的需求。在美国的战略阶段性完工后,这些需求可能会发生变化。
当前,墨西哥初步建立了为美国提供工业品的生产线,我们需要思考在东南亚初步建成这种生产线以及美国建成核心产品的生产基地后,全球贸易格局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认为,尽管受到了疫情的冲击,但美国的战略还是会在五年后出现阶段性成效,我们需要对此进行深入研判。需要关注的问题包括,在高新技术领域,美国是否会出现再工业化和关键供应链、产业链的全面回归,并且能否在政策支持下成功实现商业化;在全球层面,美国进行的近岸和友岸外包是否具备商业化和持续发展的可能等。
美国通过的《基础设施法案》《通胀削减法案》《芯片科技法案》等带来的补贴效应还没有完全耗尽,可能会继续影响中国对美国及欧洲的出口增长。但随着这些政策补贴的消失,加上美国在再工业化过程中成本降低的速度远低于中国,可能会导致一些“烂尾工程”的出现。比如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也进行了再工业化的计划,但最终以失败告终,根本原因就是利用政治力量实现再工业化的商业可行性和成本竞争可行性较低。
同时,我们也需要关注与墨西哥、东南亚等国在产品竞争上的变化。目前来看,中国与这些地区存在差别性定位,不是完全竞争的关系。但中国与日本、韩国、德国之间的竞争已经白热化,尤其是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造船等中高端制造业领域的全面升级和成本下降是非常明显的。因此,中国与这几大贸易逆差国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出现剧烈调整。同时,我们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互补性可能还会进一步提高。
总而言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可能会出现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导致世界多边体系进一步撕裂,世界传统贸易潜能持续下降,从而产生短期的产业链供应链新格局。
全球范围内成本上升带来的结构性变化更为剧烈,会导致传统三角的崩溃风险,在此过程中呈现的新的结构性变异是我们未来几年需要重点研究的,包括中国与互补性国家之间的产业升级速度差异,以及各国在中高端制造业领域的成本竞争格局。
我认为,未来五年,中国在贸易政策和战略上需要有新的定位和思考。过去几年中,我们在成本上的优势全面凸显,并且目前中国仍处于一个加速降本的过程中。
未来五年,是美国战略得到全面显化和检验的重要时期。
因此,我们一定要提高产业布局和贸易政策的契合度,同时重新思考地缘政治与经济战略。对未来全球经济的变化,不能仅从增长、通胀、利率政策、财政政策等角度来思考,还要考虑结构性变异对于政治布局带来的商业可行性和竞争模式上的变化。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校长)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版权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平台立场。
本文系作者授权平台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